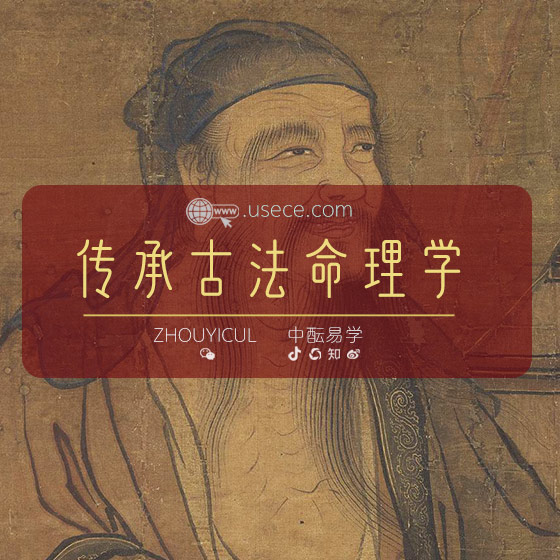
一部电视剧,尤其是一部承载着厚重历史与民族集体记忆的作品,它绝不仅仅是娱乐,更是一种文化表达和价值传递。当新版《三国》以一种“审视”历史的姿态登场时,它收获的不仅是收视率,更有无尽的争议。然而,若我们拨开“服化道”与“演员演技”的表层迷雾,去探究其精神内核,便会发现,这部剧真正的症结,并非技法之失,而是风骨之丧。它如同一面精准的“照妖镜”,照见的不仅是创作者认知的浅薄,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在权钱浪潮中逐渐失焦的价值观。
老版《三国演义》为何能成为不朽的经典?因为它始终贯穿着一条悲天悯人的底色。它让我们看到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的苍凉,让我们理解乱世中民众的颠沛流离。在那样一个人文主义的视角下,英雄的崛起,不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,而是为了“匡扶汉室”、“兼济天下”的理想。曹操既有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”的雄主气魄,也有滥杀无辜的奸贼残忍;刘备既有“携民渡江”的仁德之心,也有其作为政治家的权衡与无奈。这种对人性的平视与复杂性的尊重,才是历史应有的厚重。
然而,在新《三国》的叙事里,这种悲悯与敬畏荡然无存。它以一种近乎狂热的姿态,艳羡着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的“丛林法则”。剧中借角色之口宣扬的“乱世,是英雄建功立业的机会”,将民众的苦难彻底工具化,沦为野心家们权力游戏的背景板。这种对杀伐决断的赞美,对成功者的无底线粉饰,以及对失败者(如袁绍)的肆意践踏,本质上是一种赤裸裸的“慕强”心态。
这恰恰与我们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形成了可悲的同构。当“成王败寇”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,当金钱与权力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尺度时,过程中的道义、人性中的光辉,便都显得不合时宜。新《三国》对曹操的“洗白”,将其一切暴行都解释为“情非得已”的“必要代价”,这与现实中某些为成功而不择手段的“偶像”被追捧,何其相似?当文艺作品不再鞭挞丑恶,反而为其寻找借口时,它便丧失了最宝贵的风骨,沦为了权钱逻辑的附庸。
《三国演义》之所以动人,在于它描绘了超越个人利益的宏大情感与理想。“桃园结义”的生死相随,“三顾茅庐”的君臣相得,“千里走单骑”的忠肝义胆……这些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的篇章,是乱世中最温暖的人性亮色。
可悲的是,新《三国》的创作者似乎无法理解,也无意呈现这些人性中的高贵之处。他们的认知格局,被局限在了办公室政治般的权谋算计与幼儿园水平的阴谋论中。于是,刘备与诸葛亮之间被描绘成互相猜忌的君臣关系;周瑜沦为心胸狭隘、只会与人争风吃醋的“大都督”;英雄们的聚会,没有了煮酒论英雄的豪情,反而更像一场充斥着油腻与算计的“酒局”。
为何会如此?因为在一个极度功利化的社会里,人们会习惯性地用“利益”去解构一切。真挚的情感被认为是“虚伪”,高尚的理想被视作“作秀”。创作者将自己卑下逼仄的格局投射到英雄身上,将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,降维成了一场场蝇营狗苟的权力斗争。这种对理想主义的解构与消解,迎合了一部分观众的犬儒心态,却也如同精神鸦片,让人们在鄙夷崇高的同时,也失去了仰望星空的能力。
比新《三国》拍得烂更可怕的,是它竟然获得了不少人的追捧与叫好。这面“照妖镜”最令人心惊之处,在于它不仅照出了创作者的扭曲,更照出了荧幕前无数被无形影响的我们。
当我们为剧中人物的“腹黑”权谋津津乐道时,是否意味着我们内心也认同了“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”?当我们对“乱世出英雄”的论调深感共鸣时,是否早已对普通人的苦难麻木不仁?当我们嘲笑刘备的“仁义”是“虚伪”时,是否我们已经不再相信世界上还存有真诚与善良?
这正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崩塌的真实写照。在一个慕权慕钱的时代,人们被无形地规训,渐渐将权钱视为人生追求的主流价值。新《三国》的流行,不过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集中爆发。它以“历史”之名,行“厚黑学”之实,巧妙地为大众心中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欲望找到了一个看似“深刻”的出口。
然而,真正的深刻,从不是对黑暗的无底线迎合,而是直面黑暗后,依然选择对光明的坚守。
一部新《三国》,是一次失败的艺术创作,更是一次沉重的文化警示。它提醒我们,当一个社会开始大规模地美化权谋、解构崇高、无视悲悯时,它的精神世界正在走向荒芜。
作为每一个普通的观众,我们或许无法改变创作的大环境,但我们至少可以保留独立思考的能力。面对这面“照妖镜”,我们应当扪心自问:镜中那个为权谋算计而喝彩的人,真的是我吗?我是那个在权钱浪潮中随波逐流的跟风者,还是那个能够明辨是非、坚守正知正见的智者?
这个问题的答案,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评价一部电视剧,更决定了我们将共同塑造一个怎样的未来。


